翻阅文学史,会发现很多作家的时段划分,往往和其履踪的转移严密对应。事实上,每个作家都是一个独特的时空结合体,或曰一个时间和空间交织形成的坐标系;“情因事迁、文随地转”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汪曾祺也不例外。

笔者曾撰《汪曾祺年谱长编》,力图“为生性散漫、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可信的生活史和创作史”。《年谱》中汪曾祺的一生,呈现出鲜明的时间阶段性,而这一阶段性与其寄身的地理场域有着密切的统一关系。现在《汪曾祺地域文集》四册面世,为我们从空间角度对作家地理与其人格结构及艺术嬗变过程的互动,提供了一个生动的。
汪曾祺一生高邮乡先贤、宋代大词人秦观(字少游),他的名字隐含着地理上的“游”走、“观”览与艺术创作之间的隐秘联系。汪曾祺本人也雅好四方行走、随处流连,在他77年的人生中,履踪几乎遍及全国。不过其中很多是走马观花性质的过,就像作者自云,“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,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,毕竟只是过眼烟云。”即便如此,他的记游之作总体上也是当代游记文学中的佳品,其以独到眼光,对不同地域的景色、风物、民俗、方言饶有发现,具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意义。
不过,真正对汪曾祺的成长具有塑形作用的,无疑是居住时间最长的四个地方--高邮、昆明、、。这套“地域文集”,就是打破时间和题材界限,专从空间角度类编而成。这种类编勾画出一幅空间界限分明的版图上的四大地标。
首先是高邮。高邮地处苏中,属于“淮南江北海西头”的扬州地区。这里是吴越文化、齐文化、鲁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,而以吴越文化为主调。高邮又是大运河流经的关键之地,运河在沟通高邮与南北文化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汪曾祺身上受的影响很深,但也受到很多异质因素的濡染。在温柔敦厚之外,高邮传统中的人生意识、观念似乎沾染水的特性,比纯粹传统更为灵活、灵动。

汪曾祺在高邮出生并生活至19岁。作为其出生和早年的成长受教之地,高邮毫无疑问是汪曾祺人格的奠基之地。在此生活期间他还没有展开其艺术生涯,但是已经民风文化传统的浸润,养成朴素的审美观。很自然地,高邮生活成为其一生写作最重要的题材来源。在他1940年代的写作里,故家还未明显成为其属意的重心,但经过长期感情酝酿发酵,在新时期复出文坛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品,恰恰就是“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”的《受戒》,其后一发不可收,高邮成为他写不尽的母题。越到晚年,高邮越成为其最重要的灵魂家园和艺术领地,就像他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,“乡音已改发如蓬,梦里频年记故踪”,极好地诠释了“童年记忆”在艺术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。
其次是昆明。这里是汪曾祺的人格定型期和艺术学徒期(1939年至1946年)的生活、读书之地。汪曾祺认昆明为自己的第二故乡,他气质中的很多方面,与昆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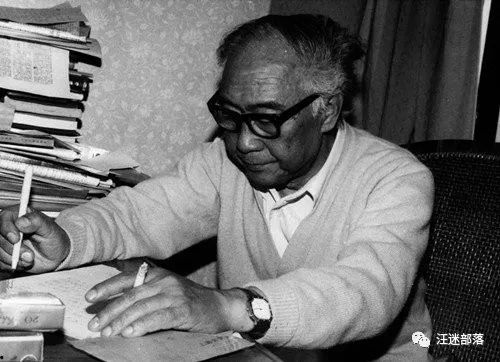
苍山洱海让他欢欣流连,带高原的独特物候风情让他目不暇接。着耗子屎和砂石粒的“八宝饭”和文林街偶饱口福的米线、饵块哺育了他青春的身体,凤翥街上的三教九流让他体验万象。当年离别时依依不舍,人到暮年又一再重游。他在昆明遇到了自己终生追慕的艺术导师沈从文,聆听了一批大师级学者的课程,不无随性地浏览了典籍,形成开阔的艺术眼界和相当的学术功底,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气质与风格。他自己说:“我生活得最久,接受影响最深,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,这样一个作家,——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,是西南联大,新校舍。”他在晚年创作大量以此段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散文,凸显了昆明生涯在汪曾祺人格和艺术中的重要地位。1990年代后期开始,伴随着一股“热”风潮的兴起,西南联大的学术教育成就引起读书界的追慕。寻绎这股之源,汪曾祺实有引领风潮、推波助澜之功。
本来上海也是汪曾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。1946年夏天起,他在这战后的东方大都会短暂寄居谋生两年半的时间,期间他寄身文教界,阅历战后万象,体察,迎来小说创作上一个小。但总体来看,写上海背景的分量偏小,“上海卷”阙如,这也是不无遗憾的事。

上海以后,是。从1948年北来谋生,在此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,编刊、写作,直到1997年终老,汪曾祺近50年的光阴在度过。作为华北大都市和著名古都,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“京派”文学的发祥地,西南联合大学的人文群体也回迁至此。汪曾祺初来时,这里是战后百废待兴的文化中心,不意稍后却成为新中国的中心。对于在师承和趣味上都有“远离”因子的汪曾祺而言,的意义是复杂的。
汪曾祺的寓居分两个阶段。1948年至1957年是第一阶段,期间他只有少数散文、特写和戏剧的试笔之作。以为轴心的文艺主潮,使汪曾祺的艺术趣味、文学理想失去依附。在找到稳妥的转轨方式之前,唯有沉寂喑哑,休笔转业。他虽未成为“专业作家”,但职业始终没出艺术界,在《说说唱唱》和《民间文学》当编辑,对说唱艺术有广泛而深入接触和积累,并与老舍、赵树理等朝夕盘桓,激活了汪曾祺心中似乎早已消泯的民间趣味。编辑生涯不意间成为汪曾祺的一个漫长的艺术发酵期。西南联大时期,他膜拜现代派,醉心先锋实验;六十年代后他回归民间与传统。正是这个发酵期里,为他实现两种径之间的跨越准备了条件。
说到此期不多的作品中的“书写”,却也常精彩。《卦摊》是1948年刚到不久所写,描写东安市场的市井万象已是穷形尽相,进入新中国时期的特写《一个邮件的复活》,以其圆熟的叙事技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《国子监》是此期散文代表作,娓娓道来,显示汪曾祺对故都历史文化的认知已达到熟稔程度。

1958年下半年汪曾祺被打成“”,当年被发配劳动,一去三年,他的人生地图上出其不意地增加了一站。
地处冀西北,蒙古高原南边缘,气候条件远比为恶劣。其中的沽源,原为一座军台,官员触罪,往往被皇上命令“发往军台效力”,实为的贬谪。汪曾祺在书上自画闲章“效力军台”,虽为半开玩笑,但推人及己、“有迁谪意”的感怀也是很明显的。
劳动生活,可以说是汪曾祺迄当时为止、也是其一生中的最低谷,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未尝不是的馈赠。正是在这里,汪曾祺平生第一次得到较长时期深入到民间生活,也第一次从生产实践和切近交往中认识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。对汪曾祺而言,是流寓地,亦是避风港。他从沉重的中了严峻;但农科所对他没有歧视,给他保留了起码的。虽然紧张的斗争和沉重的劳动为生活涂抹上压抑的底色,但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却是快乐的劳作、温馨的生活、健康的人性、动人的线年代后汪曾祺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。他歇笔十几年后,在1961年忽然写出大受好评的《羊舍一夕》,这绝不是偶然的。新时期复出后最早的一批小说和80年代后的大量散文也都以此为背景。他发自内心地歌唱这里劳动的美,人情的美,从严峻的现实中发掘出宝贵的诗意。1983年重访故地,他写下不止一首诗篇:“身虽在异乡,亲之如故土”“重来谴谪地,转能觉相亲”,这都是他对塞上高原的深情的流露。盘点汪曾祺的题材写作,很明显看出汪曾祺和有一种相互馈赠的关系,一方面,填补了汪曾祺的阅历空白,磨练了他的意志,丰富了创作题材,正如他所曾自言:“我当了一回,真是三生有幸,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”从一个作家成长成熟的角度来说,这绝非戏谑之语。另一方面,从的角度来说,汪曾祺这样一位文坛巨擘曾在这里生活并写下大量有关它的作品,这本身就是当代人文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1961年底结束的生活,开始了生活的第二阶段,直到逝世。这一阶段又以“”结束为界,分前后两期。前期,他专注本职工作——他归京后供职于京剧院,很快以其非凡才华受到高层人物的注意和耳提面命,作为核心笔杆子参与《沙家浜》等的创作。这是他一生中和结缘最深的时期,一方面风光无限,一方面如履薄冰。自然,个人化写作完全消歇了。但剧院经历对此后的写作大有意义,其一,为后期大量的梨园题材作品打下厚实的基础;其二,戏剧创作经历使他谙熟传统艺术精粹,为打通艺术门类的壁垒、建构精湛的文论思想创造了条件。
后期是“”结束,从文化漩涡里走出的汪曾祺,重新回归小说、散文创作,异军突起,在60岁成为“文坛新秀”,从此一发不可收,将近20年间创作数百万字,迎来艺术上的丰收期,成为新时期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章节。这座他生活了30年、有着久远历史文化传统的北方大城市,也成为不断书写的对象。他虽曾承认自己为“京派”,但无可否认地成为“京味小说”的代表作家,更无可地被冠以“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传人”的名号而进入若干版本的文学史著。种种情况表明,生于高邮湖畔的汪曾祺,已然从骨子里成为一名作家了。
汪曾祺生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1920年,卒于新旧世纪之交的1997年。70余年间中国风云际会、文化消长嬗变的线性历史,在他人生曲线图上投影为上述几个地标,其中包孕着一个小说家人格文风递嬗的密码,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汪曾祺、思考艺术家“人地关系”的另一个角度。

注:本文是《汪曾祺地域文集》前言。《汪曾祺地域文集》一套四卷,《梦里频年记故踪》(高邮),《笳吹弦诵有余音》(昆明),《岂惯京华十丈尘》(),《雾湿葡萄波尔多》(),广陵书社2017年5月发行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推荐: